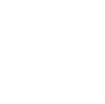援鄂日记

2020年1月29日星期三
今天是武汉协和西院接诊新冠病人的第一天,我们作为第一组接诊医生,也就是首轮医生进入隔离区,共五人,分别是领队丁新民主任医师,传染病专家苑晓冬,重症医学专家陆非平主任医师和臧学峰主治医师,老年医院呼吸病专家田蓉主任,早晨8点我们坐车到达医院,进入院区后,丁新民主任和传染病专家苑晓冬主任开始跟病区负责人协调,院感防控流程的落实以及进一步整改。陆非平主任、田蓉主任带着我开始和病区的医生协调医嘱操作、医院药品调配、病例书写等事项,一直忙到中午12点半,我们才开始吃饭。
下午2点我们开始准备换穿防护服,提前更换好手术服,冒着瑟瑟寒风(所有窗户都是开着的,方便通风),但是发现居然没有拖鞋,病区护士长紧急从手术室调来5双拖鞋为即将进入隔离区的医护人员用,1.洗手;2.戴帽子;3.戴N95口罩;4.穿猴服;5.戴第一层手套;6.隔离衣;7.外科口罩;8.第二层手套;9.戴护目镜;10.外鞋套,依照这样一个步骤下来,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左右。
穿完防护服,我们就进入到隔离病区。
接诊第一名患者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患者五十多岁女性,病情较重,送到时血氧饱和度只有70左右(正常人95),呼吸衰竭,意识淡漠,应该是缺氧很长一段时间了。没多想,赶紧救治,吸氧、补液,鼻导管吸氧,氧饱和度仍无明显提高,立马更换成储氧面罩10L/min,患者氧饱和度才逐步升高,胸部CT一看肺间质改变很明显,我们尝试了小剂量激素改善肺间质渗出。意识清醒后,患者就开始焦虑,丁主任上去安慰她,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专家,患者的情绪和状态慢慢稳定下来,血氧恢复到了90左右,患者开始告诉我们三四天没有好好吃东西,现在肚子疼,我们怕有应激性溃疡,给了保护胃黏膜的治疗,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她还跟我们挥手,感觉还挺欣慰。
接下来,大波的病人伴随着救护车呼啸而来,一个一个患者鱼贯而入,接诊护士按照名单一一核实,我们医师开始在丁主任带领下分头接诊,按照部队战时的“分类检伤”处理原则,迅速检查患者情况,如果没有危险、马上询问下一个,虽然节奏很紧,但秩序比较平稳。全部接诊处理后,按照危重程度,再评估处理,然后逐步完善所有病人的诊疗。
等第一波病人接诊结束后刚要喘口气,开始明显感觉到鼻梁压痛,但是我很清楚,再疼也不能去碰。我尽量不去想这件事,由于说话过多,眼罩开始渐渐看不清了,就像隔着一层蚊帐,一层,两层,最后也就只能对着灯才能看清CT片子。就这样我们坚持了4个小时,当接班大夫来的时候,我们总共收了13例患者,其中1例病危,2例病重。
等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的传染病专家苑晓冬主任已经穿好防护服,在里面等候我们出来,因为脱防护服是防护成败的关键,虽然之前我们反复演练,但是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而且跟我们一同出来的当地医生明显没有经过正规培训,苑主任不放心,专门来接应我们,监督大家脱防护服。摘鞋套,脱隔离衣,摘护目镜,摘外科口罩,脱猴服,摘N95口罩,脱帽子,每一步都需要六步洗手法洗一遍,最难的是脱猴服,必须要金鸡独立站稳,脱下来套脚的猴服,一旦倒了就非常危险。整个过程下来大概也是半个小时。
出来的时候发现手术服都是湿透的,风一吹更冷。后面就需要彻底洗澡半个小时……我也在感慨,我们人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分子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要想短暂的彻底隔离原来是这么难。
第一天,我们早8点半出征,晚上10点多才出来,坐在返回住所的班车上,我感觉已经体力透支了。今天我们是第一组班,最为关键的是为后续队员捋顺工作流程。在这次出征武汉抗击新冠肺炎之前,我从来没有穿过猴服,尤其穿着这么厚的防护服还要工作,确实很痛苦。值得欣慰的是,接诊过程中,我听到不止一个患者给家里打电话,“这边是北京来的专家,他们态度好,服务好,你不要在家扛着了,快来看病吧”。这次在国家号召下,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援医生,武汉同道们已经太辛苦,有我们来替你们分担,一定能战胜这次疫情。
2020年1月31日19:00
1月31日早晨3点到9点是我们值的第二个班,这个班值得有点难,自己也一直不愿意去回忆。
凌晨接班后我去巡视病房,93床的王嘉一直没睡觉,我给他测脉搏氧饱和度88%,心率120次/分,这个氧饱和度和心率明显提示缺氧,我想把他吸入氧浓度提高,但是一看已经放在了10L/min,我心里一紧,看看病人,他跟我年龄差不多,我觉得他应该还能耐受,可能有的大夫不知道,这个墙壁氧气还挺足的,10L/min并不是极限,再拧一下还能增加流量,只不过不显示,心中略有暗喜,但是很快就想到,这一点点在这种情况下简直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是我能做到的仅有的一点。
我知道,我们已经有好多设备正在往前线调集,这就是战场,我要尽百分之两百的力,把所有能做的做到极致才对得起自己肩上的责任,但愿能来点真正的呼吸机,哪怕是无创。
我转完病房所有的病人,还是有大概六七个属于极其危重的,如果条件允许应该考虑尽快转ICU病房,那里曾是我最熟悉的战场。但是现在这种条件,满病房的重病人,我能做的真的不多,我现在才真实的感觉到什么叫无助。平时的方法、技术原来都是建立在充足物资保障下的,到了这会儿,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再次回到王嘉(病人)这边,他还是没有睡,他说自己躺不下,躺下就憋气的厉害。我帮他把床头摇高,让他躺在床上几乎跟坐位差不多,可以休息一下,尽量去安慰他。
1个小时后当我再次转完一遍病房,我看他还是没睡,他说满脑子就像过电影一样,这些天的经历感觉天空都是黑色的,在急诊那会儿身边不停有人去世,但是住进协和医院我就觉得有希望,即使走了,也认了。听到这些话,我觉得他们遭受了太多常人难以理解的痛苦经历,我该做的就是尽可能让他放下所有的不必要的想法、活动,用尽全力去维持呼吸。我其实比较讨厌浮夸的人,但是这一刻,我还是做了一次。我郑重其事的跟他说,你属于重症,但是在这些重症里面是最轻的,我是专门搞危重症的专家,平时跟你这种状态的病人打交道最多,你放心,我肯定让你安全回家,你要是信我的,这会儿就踏踏实实的睡觉、休息,只有休息好了,自身免疫力上来了,这个病才有的治,要不然我也没办法了。说完,我又把他按倒,把枕头竖着放,让他可以靠在上边,不至于来回滚动。
这次他听了我的话,我帮他把床头灯关掉,他安静的躺着。我开始回头想起刚才自己夸下的海口,我心里真是没底气,在这个危难时刻,我也只能做这些了。不过听说很快就要有呼吸机了,到那时,我们应该能让患者更安全,给他们更好的治疗。
2020年2月1日
今天是第三个班,接班后没多久,我先去看了收治的第一个患者闫庆芳,她还好,呼吸困难比之前有所缓解,但是稍事活动脉搏氧饱和度就会降低。我们上一个班从病房出来之前收治了一个极其危重的八十多岁的老年患者,他进病房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场的所有医生一致的判断都是“很重”,应该转ICU了,但是没有办法,ICU没有床位,经过我们初步治疗,当我们走的时候他已经苏醒,虽然还是缺氧,但是能表达自己诉求,我们还觉得非常欣慰,也觉得很有希望。但是,当我走进病房的时候,患者头左侧歪斜,手里还端着饭,嘴上扣着储氧面罩。我抓紧上前去拍患者肩膀,没有反应,我第一反应是心跳呼吸骤停了,我立即喊人,然后把床头放平,尝试心肺复苏,但是我发现患者体温已经有些凉了,至少要有2个小时了。虽然我们还是奋力抢救,患者还是走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给了你一点希望,又在你面前扎破!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有担心他会出现心脏意外,联系了心电监护仪,可是他居然没有等到心电监护仪的到场,结果悲剧真的就这样发生了。所以碰到老年有基础疾病心脏病的患者,一定要加强心脏方面的监测,条件允许应该给予持续心电监护,筛查心肌酶、完善心脏超声等心脏情况筛查,并且必须加强巡视才行。

2020年2月5日
昨天是我自己一个人和当地医生一起值大夜班,我心中反复想着,我是唯一一个专业的,其他的老师仅仅是能帮助我,我必须自己承担,一定要考虑全面。为此我早早的来到病房,熟悉患者情况,询问当班老师里面白天发生的事情。当夜里1点之后,顺利交接班之后所有前一个班的老师就离开了,我便开始组织我们当晚值班的老师分工,有负责接听电话和呼叫器,并开医嘱的老师,有特殊情况备班进隔离病房的老师。而我就做好进去的准备,并继续挨个病人反复查看医嘱和化验单结果。接班后我就第一个进去,我巡视病房发现131床呼吸频率比较快,40次/分以上,而且氧饱和度难以维持在正常范围,我第一反应是这个病人病情危重,应该紧急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了,但是我们病房没有这个条件,转ICU病房,但是白天多次联系均无床。这个病人呼吸频率在40-60次/分,脉搏氧饱和度仅有80%左右,实在是太危重,要不是年轻,身体条件较好,估计早就挺不住了。
我心里不停的在问自己怎么办?我还能做点什么?我一直陪在她身边,帮她调整高流量鼻导管,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我把邻床的氧气管路也给利用起来,给她多扣一个储氧面罩,但是作用有限。白天反复追问过科室主任和护士长,目前没有呼吸机,无论是简单的无创、还是功能齐全的大型呼吸机,目前手边除了经鼻高流量,储氧面罩外,已经没有其他的设备可以利用,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我又给床位紧张的ICU病房几次打去电话,一再帮她。最后得到的结果仍然是尽力,目前没办法转。
没别的办法,我只能给其丈夫打电话报了病危,患者的丈夫和我年龄相仿,三四十岁的样子,得知情况后在电话里嚎啕大哭,131床患者的母亲就是我们之前的42床阿姨,她刚在我们病房去世,而患者本人又这么重,电话中我得知患者的丈夫也是新冠患者,只不过目前病情还算轻,不需要住院,还得在家照顾老人,因为年龄相仿,那一刻我真实的感受到他的痛苦和无助,我尽力安慰他,我承诺,“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她。”回到患者身边,我再看患者状态,她反复说憋气,有东西咳不出来,我开始帮她叩背了20分钟,终于咳出了些痰液,看着像淡血性的粘液,粘在嘴边,我帮她擦干净,继续鼓励她,让她放轻松,一口气一口气的呼吸,不要使劲喘。但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这样,我陪在她身边终于等到了天亮,从隔离病房出来前我就给外面的值守医生打电话,必须尽全力协调将这名年轻的患者转入ICU,要不然没有希望。洗刷完毕,我又给ICU打过两次电话,这次找到了高年资医生,我告诉他这个病人真的很年轻,抢救后更有可能存活,意义重大。同时我也拜托病区张主任反复打电话,就这样,在早晨交班结束后,大概10点左右这个病人成功转入ICU病房,顺利插管上呼吸机支持。我们也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回去踏踏实实地睡一觉了。
2020年2月12日星期三
希望就在眼前
今天下夜班,因为交接时间过长,错过了班车时间,一路上骑行返回,看到路上有军车、救护车,还有几辆稀稀落落私家车,与刚到武汉时的“沉寂”完全是另一幅景象,我们亲眼看到了这座城市如何从“病痛”中逐渐苏醒过来,因为疫情,大家要么被病毒压垮了身体,要么被病毒压垮了精神,现在因为全国的总动员,各种物资供应和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的加入,让整个城市正在加速恢复中……
一路骑行,不禁想起了刚才查房时看到的41床老阿姨,她是我们接管协和西院12楼病区后收治的第一个病人,进门时人一分钟喘气40多次,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只有74%(正常人95%左右),严重的呼吸衰竭,在初步纠正了呼吸衰竭后,她嘴里还断断续续的念叨着“别让我难受了,活不活的无所谓了,我受不了,我憋死了……”。很难想想她们是遭受了多大的痛苦与无助,能让一个50多岁的人就放弃生的念头。
虽然见惯了危重病人,但是面对全新的疾病,谁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也没有治好的把握。从专业的角度,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命体征,我必须让她降低所有不必要的“氧耗”,首要的就是要争取她的配合,硬着头皮也要逞一次强,“我们是北京来的专家组成员,是专门治疗这个病的,您的病对我们来说属于轻的,好好配合,一个周就会好的……”,就这样不停的絮絮叨叨,让她吃下定心丸,专心配合治疗。
“一口气一口气的呼吸,不要怕憋气,这是人的正常反应,只不过身体太着急,你需要控制身体,不能让身体控制你,要不然就进入恶性循环了”;
“不要怕尿床,我们帮你换尿垫,没人会笑话你,现在的病情不允许你下床,熬过去这两天,稍微恢复一点,咱就可以去厕所了 ”;
“要好好吃饭,当成一项任务,不要怕吐,吃三口,吐两口,还赚一口呢!”
…………
她也确实非常努力、非常配合,我们的任何嘱托,她都当作圣旨去执行,克服了一切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
从刚开始储氧面罩12L/min,脉搏氧刚刚能到90%,再到3天前的94%;再到今天早晨储氧面罩7L/min的情况下,脉氧能达到97%,她确实做的了,她成功了,希望就在眼前。
虽然一夜未眠,虽然还有好几个重病人未脱离危险,但是,好在41床阿姨还好,她挺过来了,按照我们希望的样子在一步步恢复,就像整座城市一样在逐步恢复,希望就在眼前。
2020年2月20日
昨天本来是个非常喜庆的日子,经过20多天的救治,我们一部分重病人可以脱离吸氧,复查满足出院指征,我们病区一口气出了10个病人(病区总共50张床位,患者数50例),能看到自己收治的病人好转出院,我们大家很受鼓舞,所有大夫下午都去送患者回家,我们开心的合影、留念,还有领导和患者代表现场有感而发的演讲,大家都很高兴。当天晚上我是夜班,凌晨1点到早晨9点,我晚上睡了2小时睡不着了,感觉也是激动。但是翻看了我们群里的消息,发现出了10名患者,又来了11名患者。那天前夜是我们医院的苑晓冬主任和张捷大夫,两位老师都比我大很多,我觉得我作为年轻的大夫应该主动替他们分担点,我就提前吃了点东西,11点出发去接班了。平时都挺冷的,那天晚上天气也不错,我本来是自己哼着歌,后来一想,给自己留个纪念吧,录制了一个小视频。
2020年2月22日
早晨巡视病房,我去看病重的42床老先生的时候,看见41床闫阿姨显得特别焦虑,我关心了她几句,顺便测了个氧饱和度,储氧面罩5L/min,氧饱和度已经能达到95%,相当不错,我鼓励了她几句,她就是我们开病房收治的第一例患者,入院的时候人是意识不清楚的,储氧面罩极限情况下(12L/min)刚刚能达到90%,现在比来的时候已经好多了,但是她特别脆弱,不停的问我为什么还不好,她为什么现在连摘下来面罩吃口饭都会喘气的厉害,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我在她床边多站了一会儿,让她把情绪发泄一下,然后跟她解释了她目前的状态,我跟她从头回忆了她所取得的成绩,她来的时候储氧面罩极限状态刚能喘的稍微轻一些,我教他如何平稳控制呼吸,避免陷入恶性循环,她做到了;她当时稍微动一点,就会憋气,需要歇半天,我让她放弃不必要的尊严,在床上解决大小便,让我们护士帮她处理,她也做到了,现在可以在床边自行解决;她吃不下饭,吃了之后老是会吐,我们跟她说,吃三口吐一口还赚两口,现在她能自己吃饭了,只不过稍微有点缺氧……
说着说着她抽泣的声音少了,我说她是这一层危重病人中最听大夫话的,恢复最好的,她应该把她的经验分享出来,让更多病人像她一样配合医生。那天我试着给她把储氧面罩更换成了鼻导管,她活动能更方便一些,人也更有信心,还给她拍了一张照片,她后来说等后面好一些可以给大家录个像。

2020年3月15日
昨天又是一场硬仗,按照抗疫指挥部统一安排,原本说是要来十几个病人,结果来了10个,我本来是晚上8点接班,就提前下午早早来医院了,结果一到医院发现张捷老师也来了,正好有一位媒体的老师要进病房,我们就让院感专家苑老师负责媒体老师,我跟张捷老师负责收病人,我们匆匆换完衣服,进了病房安排好收治流程,就碰到上一个班的刘婷大夫,她是妇产科的,我跟张老师接过她手中收集的资料,大概问了几句之后就让她走了,她感动的不得了,我在想,一个妇产科刚毕业的小大夫,面对这个疫情也真是被逼上梁山,她肯定会尽力,但是一方面觉得她身材太矮小,体力会不支;另一方面也不太放心,她抓不到重点,放走她,反而更踏实。
然后我就开始一个一个病人过,我负责5个,张老师负责5个,拿到床号后,我从最西头病房朝东一个一个过。打招呼、测脉搏氧饱和度、测心率,然后询问目前最主要不适,筛查有无危重迹象,没特殊的,再仔细问病史以及治疗情况。今天的眼罩虽然涂了防雾液,但是可能说话太多,另外天气也有点热,还是不停的起雾,很难看清。非常奇特的是,就在眼罩中央位置各留了一个空可以看资料。平时我们收治一个病人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碰到麻烦的可能会更长。这次好在病人都带了一份出院小结,可以作为参考,只需要仔细问目前状态、症状,所以还是比较快,大概用了不到3个小时,所有收治工作收尾。
等看完所有病人,我又回头捋一遍,特殊情况标注一下,然后就开始往外传送,嘱咐外场的老师帮忙开医嘱,并记录病程。
这一次,我把我们总结的俯卧位在几个严重缺氧的病人中进行了实践,患者依然感觉不错,而且脉搏氧饱和度确实有改善,我觉得自己捡到宝了,我一定好好总结一下,但愿能帮到更多病人。